旁聽民眾 觀的疏離,審的暴力
林倩如 高中教師
一個公民與社會科的老師,沒有做過一天法律系學生,卻要在高中課程中教授法律長達一學期(若加上教育部所定訂的選修課程,甚至會需要更久的時間),這件事情如果讓任何一個法學系教授知道,應該會覺得這比電影危險遊戲(Dangerous Minds1)所陳述的內容更加令人戰慄。
若說美國大法官 Oliver Wendell Holmes 的名言「法律的生命不在邏輯,而在於經驗」讓人震懾,似乎也就訴說著受到社會體系控制、規約的人民,其實企圖從體制中尋得一點權利與情感的自由;然而,若證諸近代法律體系的發展,卻會發現系統的增生已經揉雜了太多人類的恐懼、偏執與愚昧,以至妄想在人造的體系中去擁有神才能擁有的洞見。也因此,在現實生活中運作的法律多半只是使系統中的個人僅如同平庸的量刑機器,而接受審判的個人多半無法擁有自主的靈魂與主體的能動性。
回到歷史的發展系譜,近代的陪審制起源於英國,隨移民漸次進入美國、並在法國大革命後,作為民主政治的重要象徵而廣佈歐陸諸國;然而,德、法卻先後於 1924、1941 年廢止陪審,改行參審制度。除了陪審制度花費不貲,更因為大陸法系國家對於刑事法解釋、適用之發展,已經遠遠超過了陪審團所能處理的程度;法律在適用與事實認定難以截然區分,若還堅持讓陪審團獨力認定犯罪事實的有無,不但有事實上的困難,更可能造成法律解釋、適用上出現問題,進而引發違憲的危機(張永宏,2011:21)。
但無論是參審或是觀審制,對我而言都是人民參與公眾事務、貼近他人,重新定錨、以作為互為主體性的基石。在這種過度天真的想像下,不但沒有清楚理解民間與官方版草案的差異,也從未參加過官方/司法院版本參審制的旁觀者,在兩天的模擬法庭之後,對於這一個案或司法系統的革新,留下許多等待開啟的疑問,並企圖尋求著更多的填補與思考。
首先,必須指陳的是在這次的個案,犯罪鋪陳線索的缺乏,以及警方在執行過程中的說明並不夠明確,致使在唇槍舌戰的檢辯攻防中,旁觀的他人無法清楚知曉:警方如何調查消息來源所提供的犯罪情資,而檢方是在何種狀態下提出聲請、進而使法官認定可以開出搜索票等細節。
例如,當女性被告堅稱郵寄之物件是骨董時,在庭上並沒有托運單載明該物的價值、品項,以確證該物是古董,進而確保被告所言屬實;甚者,當檢方想要證明女性被告有協助運送毒品的動機時,相關的資產負債、銀行存款、交友狀況也應該清楚羅列,而不是只是透過含沙射影的方式證明女性被告曾有多次收受男性被告餽贈等情事。而這些缺漏的證據,使得法庭上的陳述脫離了庶民的生活經驗,當然也使得諸多證詞難以被確切檢驗、進而確證論據存在的合宜性。
其次,在程序中沒有被呈現、卻是令我更好奇的是:女性被告的問訊過程中是否運用不正訊問,以及有無律師陪同?男性被告的附帶搜索是否也仍符合正當法律程序的規定?一般而言,坊間刑法與刑訴法的參考用書中大多慷慨陳述無罪推定的基本原則,然而在充滿偏見的社會中,人的脆弱來自於他/她的出身與眼界,執法過程中的個體都是被意識形態所滲透的個人,若無法透過法律去約束、規範權力的行使,則會使得國家暴力橫行無阻。
另外,此次的陪審員多為自主報名,分析其組成當中有超過 20% 是無論如何均堅決反對廢除死刑,不但多半受有高等教育,且當中有超過半數以上是生理男性;是故,此一團體的思考無論如何是有可能脫離一般民眾的思考,也不符合社會組成的多重樣貌。但在這樣的情境下,居住在帝寶、與頂新魏家往來過從甚密的男性被告,面對的挑戰是:如何說服陪審員、法官,他根本無需運毒以「換取幾十萬的零花」、賺取「20 萬中的 30% 年利率」;而女性被告則需面對的任務則是:在這一公共空間中,去重構出關懷倫理學中所描述的,擁有差異性別角色與認同的個體,在情感、挑逗與社會交往的互動中,的確有不同的生存之道。然而,除了達致互為主體性的可能性之外,更困難的是我們能否真的可以接受:無論出身是富貴、貧窮、亦或前科累累的被告與原告,都有權利、也可以勇敢地為自己辯護,而無需擔心更多的社會責難和批評?
綜上所述,可以想像法庭上的困難在於:法官要如何持平地建構民眾對於財富、階層流動、性別的想像,甚或帶領人們思考每一次的「偏差」行為,究竟是「犯罪」或是「創新」的行為模式等;除此之外,還要面對繁瑣的準備、選定陪審員程序,訴訟的效率與品質是否得以在「效率至上」的工業化時代兼顧,端賴承審法官心中的量尺,以及對《刑法》背後所代表的權力所敬持的謙抑之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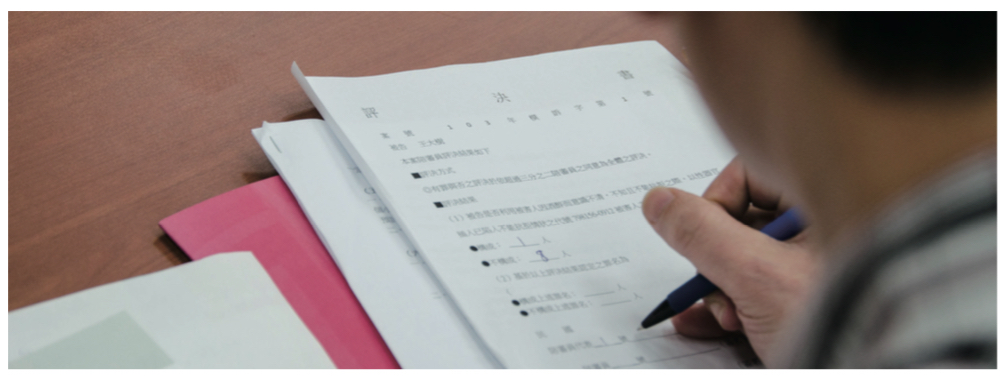
陪審或參審作為最嚴刻的法治教育,不僅是單純地將法律素人置放到法庭,去滿足個人或法庭至高無上的權力慾望而已;還必須包括在公民的養成過程中,能夠清楚地將事實與意見的分離,努力不被一個人所呈現出的階級、習癖、文化或社會資本所迷惘,盡可能努力剝離原本對社會規範「視之為理所當然」的假定,重新回到人性中去探索本來就存在的鄙俗與可貴。
然而,這些事情在現今迷信「專家」的社會氛圍中,給了權力菁英太多的空間、卻又剝奪了太多底層人們的可能,而國內外學者 David Garland(2001/周盈成,2006)、許華孚等人研究中(2005、2014)也再次都進一步證實了人們在不確定的年代、高風險的社會,都矛盾地想要藉由更嚴格的法秩序去打造起更高的「安全」圍籬。是故,「今天,我是法律的法官,你們也是法官;你們是事實的法官,將由各位來決定事實是什麼!」這句話不應只是對陪審員的諭知,也是在生活情境中,無論是在法庭內外的我們都需要銘記在心,總是盡量學習著傾聽、觀察,並且在做任何判斷前,都要盡所有可能地卸下權力的虛妄與膨脹,反身面向自己、潛心想像另一種可能的生命狀態與伸展姿態。
- 為 1995 年由美國導演 John N. Smith 所執導、改編自真人真事事件的電影,主要敘述一個海軍退役參的軍官蘿恩,轉行投職於英文教師,故事從在面對一群活在社會邊緣、墮落度日的學生開始。
參考資料
- 周盈成譯(2006)。《控制的文化:當代社會的犯罪與社會秩序》。台北:巨流。(原書:David Garland(2001).CRIME AND SOCIAL ORDER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 張永宏(2011)。〈人民觀審制度的時代意義〉,《法扶會訊》,34:20-22。
- 許華孚(2005)。〈監獄與社會排除:一個批判性的分析〉,《犯罪與刑事司法研究》,5:191- 235。
- 許華孚、孔健中、黃千嘉、劉育瑋(2014)。〈從底層階級到危險他者的「遊民」〉,《犯罪學期刊》,17(1):1-39。